朱生坚|做一辈子也行 | 孙甘露

文章插图
【朱生坚|做一辈子也行 | 孙甘露】叶辰亮 摄
很久以来,我有一个巨大的遗憾,就是不会任何乐器,事实上,就连简谱都不识。我在老家上小学和初中时见过的乐器,只有学校里仅有的那一台脚踏风琴——这么说也不太准确,因为村里婚丧嫁娶所用的锣鼓也是乐器。初二那一年,来了个刚从大学毕业的物理老师,兼任团支书,他准备组织第一次集体活动,竟然问我家里有没有钢琴、能不能搬到学校操场来给他用一下。真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反正,这么说吧,在我眼里,那些会某种乐器的人,简直就是有神仙福分的妙人儿。退一步说,能坐在旁边翻曲谱,也让我艳羡不已了。
我的这个想法受到了张文江老师的批评。是的,我也知道这是不对的。有人说我矫情,那却是我不能承认的。但是,就像很多根深蒂固的念头一样,认识到它的错误是一回事,要把它剔除干净,还需要一点特别的体验才行。
终于,在孙甘露的《时光硬币的两面》里,他在莫斯科普希金纪念馆看到了“大厅里的一架演奏会钢琴。我无心多看普希金的老师茹科夫斯基家里的桌椅板凳,兀自放肆起来。管理员,一位老太太,向钢琴走来,我以为是要驱逐我,但是她慈祥的眼睛里居然含着泪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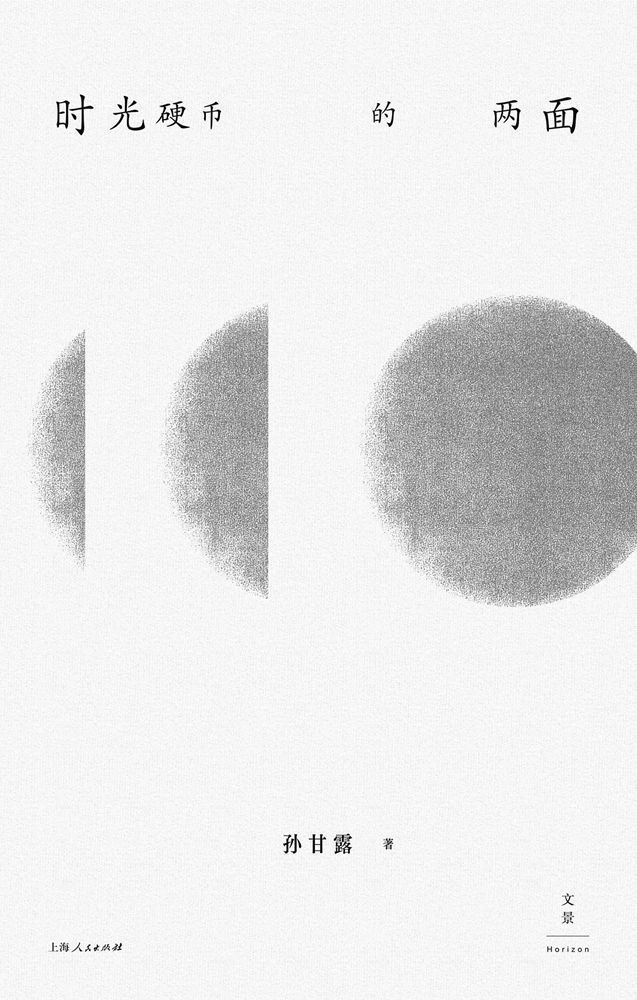
文章插图
在以每小时306公里的速度插入苏北平原的高铁上,我合上书,在遐想中“兀自放肆起来”。还不到一分钟,我就做出一个无耻的决定,把这段文字,哦不,这段经历当作我自己的。从此,给我的遗憾划上一个完美的句号。虽然我更喜欢的是大提琴,而不是钢琴,那又有什么要紧?
我这么做是有理由的。按照某种理论,一部作品并不是在作者创作出来的时候就算完成了,受众(读者、听众、观赏者)的欣赏、理解和阐释,都是作品的一部分。而作品和受众之间发生的关系是相互的。孙甘露引用了巴伦博伊姆的话:“当你阅读歌德的时候,你会觉得自己是德国人……正像我指挥贝多芬或布鲁克纳的作品那样。”反过来说,读者把作品里的,或者说把作者的东西据为己有——当然,不能分版税——也完全天经地义。这是阅读的权利或福利。
顺便说一句,我们有理由认为,相比之下,在各式各样的受众里头,阅读者的主动性是最强的,你可以随便浏览,可以纵情想象,甚至可以用不同的方式续写或改写,不像你看手机视频的时候,你能做的只是对着它傻笑。最重要的是,一篇文章、一本书,要是不对你的口味,你只要瞥上一眼就知道了,但是对手机视频之类就不一样了,你常常不得不浪费存量有限的生命,因为只有看到结尾才会发现这一段脱口秀根本就没有你所期待的包袱,或者那一段视频有多么的低级趣味或无聊乏味,没让你恶心反胃就算好的。
写到这里的间隙里,正好在手机上读到了一位朋友对孙甘露的采访,她引述了他对于阅读的强烈愿望,“不分昼夜,不论时节”。似乎还可以加上几句:也不分阅读对象的种族、肤色,也不论男女老幼,是死是活。就在这本《时光硬币的两面》里,随处都可以窥探到他的阅读的体量,还真跟这位炮兵部队子弟进入任何一个空间都不容忽视的气场或体格成正比。这是一句实话,没有毛尖式的夸张和隐喻。然后,你会知道,他写出那些作品——不只是那些小说,还有收录在同时出版的另一本书里的那些诗——一点都不奇怪,而他给上海这座城市营造的读书活动也全都是顺理成章。“从某种含义来看,城市本身就是一座图书馆。街道是它的走廊,建筑物是它的书架,每一个窗口都是一部书,而我们同时扮演了读者和书中人物这两种宿命的角色。”他在这里隐去了作者,你可以仔细品品。这篇以“写作与沉默”为题的文章的主题正是阅读和写作之间的关系,他在结尾写道:“他们的不写和其余人的写恰好构成了今后漫长努力的全部背景。声音和沉默正是一枚硬币的两面。”
推荐阅读
- 教育部|吕梁市教育局通知:做好寒假期间“双减”工作
- 什么|广州入户心得:我不是学霸,只是听话照做了~
- Offer|大学申请专题|英国大学网上申请需要做好哪些准备?
- 申论|22年首次报考执业药师的“小白”,建议你们这么做!
- 社会|7岁男孩“憋着不能哭”令网友破防,我们应做些什么?
- 教育|强校带弱校,怎样做更好?
- 教育|好好说话,是父母毕生的修养,请你一定要做好4点
- |班主任坦言:双减后,容易逆袭成学霸的孩子,父母都做对了一件事
- 大学|金融专业美国硕士留学需要做什么准备?
- 大学|中考分流后,最吃亏的是“开窍晚”的男孩,父母能做些什么











